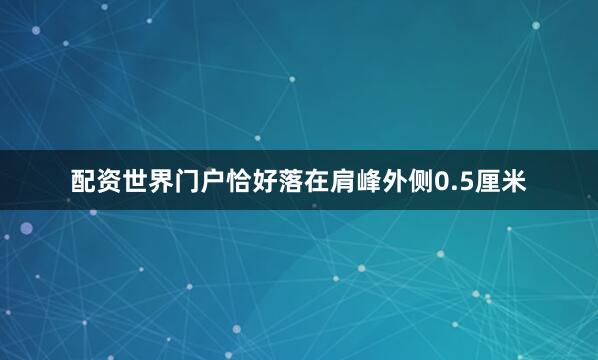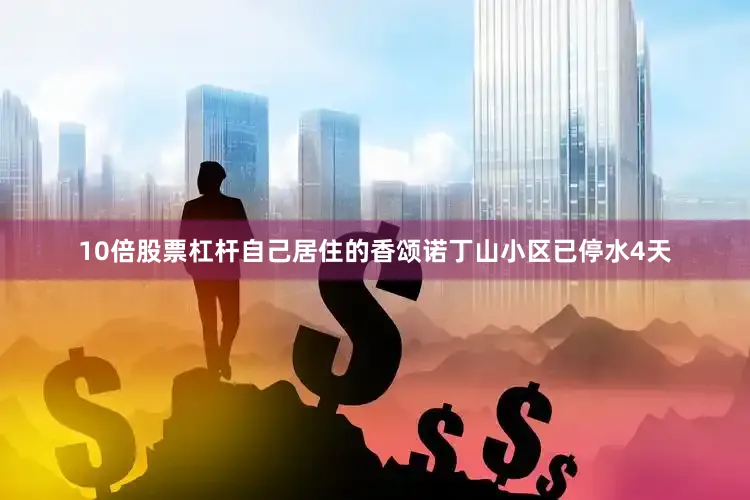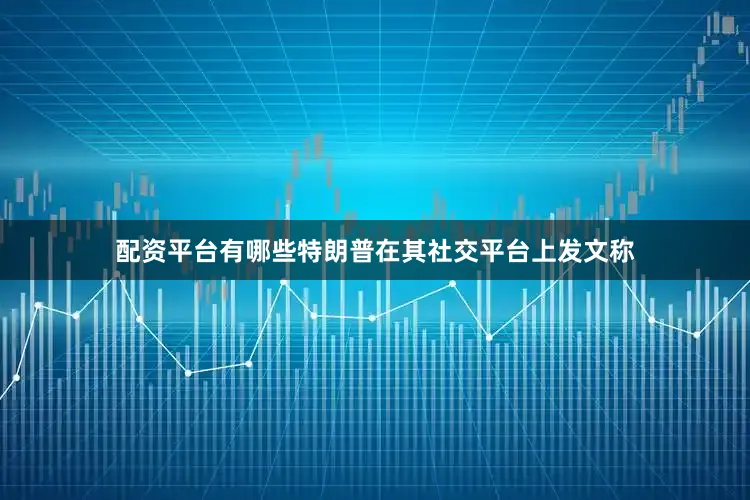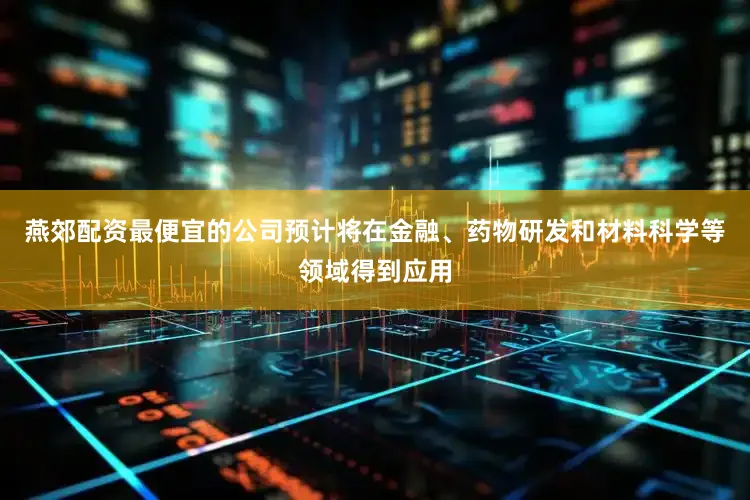当清帝国的旗帜在1912年从全国城门褪下时,德占青岛的大鲍岛并无锣鼓,却在华商的院落里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交接。广兴里——这片里院巨构的“心脏”——从广东商帮领袖古成章的名下,转到了江浙“三江商人”周宝山的名下。交易之外,更像是一场权力的更替,一次在德国法与华人“规矩”共同作用下的体面安排。是年九月三十日,孙中山来青岛,入海关而出,第一站即至广东会馆致辞,同乡簇拥;但在会馆之外,更大的力量顺势流转,沿着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之间的街角,悄然改变了这座城市华商的版图。

城市边界与会馆秩序
德占初期的青岛,华洋分治,法令与习俗彼此交错。对于华人群体,会馆既是“家”,也是“官”。广东会馆在芝罘路落成的那年是光绪三十二年,1906年,它立规矩、聚香火、办集事,像一个小小的准政府与准法院。三江会馆则在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应运而起,周宝山与丁敬臣等人联袂筹建。落成典礼之隆重,连山东巡抚杨士骧和胶澳总督都沛禄(Oskar von Truppel)也同日到场,这不只是面子,更是权力的背书。在会馆这个组织形态里,乡缘即纽带,商规即契约,礼法交织,彼此承认又相互牵制。

两股商力的相遇
广兴里最初的故事,得从更早的1901年说起。古成章,广东香山人,“大成栈”的经理,走南闯北的嗅觉引他在博山路买下地皮,盖起两层商业楼。那时大鲍岛还在泥石间翻身,他的楼像旗杆一样竖起,成了广东商帮在青岛的第一面旗帜。这股南来的力量讲究速决、靠胆识;而周宝山,浙江慈溪人,经营“周锐记”,背后是一个横贯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安徽的内地网络。他代表的是“三江商人”的组织力与资本厚度。一个靠“开山之作”,一个借“后来居上”,两股力量在同一个地盘上逐渐相向而行。

从“商务公局”到“华人信任”
1910年是胶澳官场与华商关系的拐点。德国总督府撤销了原有的“中华商务公局”,改为直接委任四名“华人信任”,专门协助处理华人事务。名额分配清晰:齐燕会馆占两席,三江会馆与广东会馆各得一席。古成章与周宝山,双双进入这四人的核心圈。清政府颁布《商会简明章程》,青岛的三大会馆遂呈报“胶澳总督”批准成立“青岛商务总会”,其后“青岛中华商务总会”在天后宫设会址,以章程明文,连结会馆与商界。表面看是机构更替,实则是治理工具的升级:德方需要一个能沟通华人社会的中介,华商也乐见一个承认其自治的渠道。

革命的鼓点与北帮的退潮
辛亥革命的声浪传到海边,1912年间,北方商帮——齐燕会馆——因与清廷关系密切而受冲击,这是权力版图的自然后果;而广东商人本应得势,毕竟孙中山乃同乡。9月30日,孙中山到青,拜会海关后即赴广东会馆与同乡交谈,后在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发表演讲,场面热烈。但政治的亲近并不自动转换成账本上的数字。贸易中断的风浪、资本调度的难题,或因革命未定的局势,或因个人决策的失手,让南来老牌的广东帮在经济上渐显疲态。商场如潮汐,退进之间,眼光与胆识皆要与时局匹配。

一桩体面的交易何以达成
就在这一年,一个足以震动大鲍岛的决定落下:古成章将广兴里连同尚未完全建成的地皮,转让给他的竞争对手周宝山。外界看是一宗买卖,内里却是“规矩”与“法”的双重作用。德占的地政科需要白纸黑字的德文契约,价格、范围、权属都得明明白白;而在会馆的圈子里,还要有另一份更能约束人心的中文“君子协定”,承认“开创之功”,保证“体面退出”。这类契约可能在三江或广东会馆的密室中,由几位年长的商会长老见证,讨论不止一次,谈的不是墙砖,而是未来的秩序。古成章得到现金,保全实力与名望;周宝山接手地块,确立新霸主的姿态。这种处理方式合乎“和为贵”的老理儿,也合乎总督府的法条,法律与人情彼此咬合,成就一次无声的权力接力。

广兴里的重生
周宝山拿到广兴里后,并非原样维持。1914年,他在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三面合围扩建,一座更宏伟、布局更完整的新广兴里拔地而起。与其说是建筑升级,不如说是三江会馆势力鼎盛的明证。里院一面临街,商铺排列,另一面深入巷里,居住与交易互相渗透,这是青岛华界“生活—商业”一体化的典型画法。建筑的每一根梁柱,背后都是资金与网络的实证。

从档案里看见余波
所有权的变更被认真记录。德国法院与地政部门的登记,留有契约与存根。后来的史料中,还能看见“第四任业主——张仲馀土地所有权证书存根”的踪影,说明广兴里经历了再次易手。波澜不在纸上,在纸背之后;每一次产权更迭,都是城市经济结构微妙调整的回声。

制度小科普:殖民法与商帮规矩的相互咬合
德占青岛的法律体系强调契约与登记,这是现代地权的“硬法”;而华人会馆的章程、同乡之间的约定、商帮内部的纠纷化解,构成了另一套“软法”。法社会学称之为“法律多元主义”:国家法并非唯一来源,团体规范同样具有约束力。在广兴里的转让里,两套秩序并不彼此否定,而是形成一个嵌合结构。德文契约保证产权流转的公信力,中文约定保障人在圈子里的脸面与信誉。对商人而言,失信于会馆比违约于官府更可怕;对总督府而言,能找到被社群承认的“华人信任”,远胜孤立地执法。“礼法合治”,古人说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在殖民地语境下依旧成立。
从四名“华人信任”看权力配置
1910年的“华人信任”名额分配,透露了当时的权力数学:齐燕会馆两席,广东与三江各一。齐燕的北方背景与官府联系使其当时占优;但辛亥之后,它受冲击最大。古成章、周宝山的共同进入,既是个人声望的认可,也是两家会馆在治理架构中的锚点。随后,三大会馆联名申请成立“青岛商务总会”,三江与广东分别占据地盘与话语。会馆不只是乡缘组织,更是政策快递站、纠纷协调所、信用认证中心,它为德方提供“可对话”的对象,也为华商提供横向协作的通道。
双雄对照与命运的拐点
若把时间摊平,古成章与周宝山呈现的是两种商路的对照。一位在1901年先手落子,嗅到大鲍岛未来,以广东会馆(1906)为阵地,凭个人领导力拉起队伍;另一位在1907年携资本与网络入场,三江会馆起步即有官方加持,善用组织架构稳步推进。到了1910年,两人皆获总督府“华人信任”的承认,话语权相近;1912年革命来临,政治亲近却未必转化为商业优势,广东帮未能借势扭转走势;而周宝山在1914年用新广兴里的拔地而起,兑现了“后来居上”的承诺。双雄并立的格局一度呈现为“一南一北”:南边广东会馆,北边三江会馆,各有领袖,各守地盘,彼此竞逐又彼此需要。命运的拐点常在时代的裂缝里,谁能调整航向,谁就能接住新的风。
会馆里的司法与市场的温度
在广兴里这场交易的背后,是会馆作为“准法院”的运作逻辑。争议不必闹到总督府法庭,先由会馆调处;条款不必写到最硬,先考虑彼此体面。它与德国法并行不悖:一份德文契约向官署备案,一份中文约章在会馆里口碑流传。这样的双轨保证了交易不仅合法,更可持续。对青岛这样一个被殖民却高度商业化的城市而言,这种多元秩序让市场有温度,让权力有边界。
广兴里之外的城
将视线稍微拉远,可以看到更多细节。1907年三江会馆落成不久,清政府的《商会简明章程》为各地商会正名,青岛的三大会馆联手上报,“青岛商务总会”获胶澳总督认可;同一年,日后在天后宫设址的“青岛中华商务总会”成为华商公开的议事平台。1910年的机构更新与1912年的政治震荡,像是两次大潮,拉扯着商帮的兴衰。古成章在鼎盛时被委为“华人信任”,周宝山在崛起中亦名列其间。孙中山到访,广东帮得以在政治上重振士气;但是账本与工地决定胜负。周宝山在会泊路、易州路、高密路的三面合围,不只建起楼院,也围拢了三江商人的话语权。
尾声:在青岛的风里看见人情
广兴里的契约后来还在德国法院与地政档案中被翻检,连张仲馀作为第四任业主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存根也成为史料的旁证。若说这桩交易给予我们的启示,便是看见城市的中国面孔如何在殖民制度的缝隙里生长:他们懂白纸黑字,也信“人情世故”;他们敬重开创者的功劳,也承认后来者的实力。权力交接不必轰鸣,商帮博弈也能“礼下庶人”。这座里院的变更,既顺从德国当局的法律,也遵循华商社会自立的规矩。法律多元并非抽象学说,而是落在一砖一瓦的广兴里,落在一纸契约与一声叩门之间。风从海上来,人从四方来;有规矩的交易,有温度的秩序,才是商人社会真正倚重的城墙。
配资网上开户,配资账户创建,配资股票论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